“为什么跨性别男性/男性化的青少年总是被无情地描绘成‘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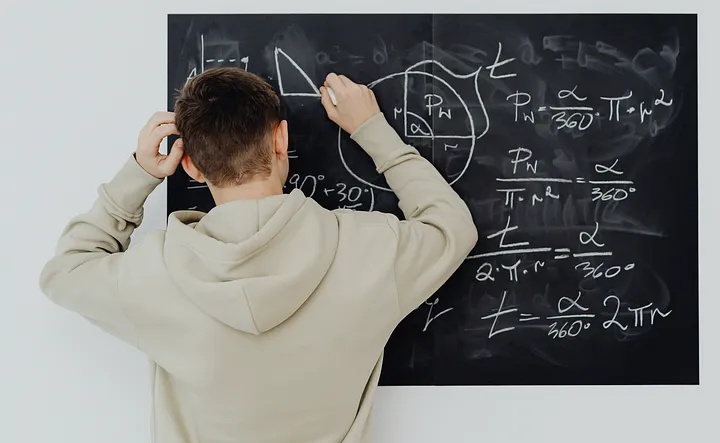
在一篇配套文章《所有反驳“跨性别社会传染”的证据》中,我提出,越来越多儿童认同为跨性别者的现象并不是因为跨性别身份突然变得“传染”,而是由于反跨性别污名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跨性别意识和接纳度的提升。
然而,“跨性别社会传染”或“ROGD”(快速发病的性别不安)的支持者常常提出的一个论点,我并没有在那篇文章中讨论,因为我认为它需要进一步分析。具体来说,支持者会引用最近在跨性别男性/男性化青少年(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AFAB)与跨性别女性/女性化青少年(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之间比例的变化:虽然历史上后者更为常见,但如今前者似乎占了更多比例。这种变化被描绘成一种异常现象,需进一步解释,而“跨性别社会传染”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同样可以通过“污名减少假说”来解释——我将在这里为此做出论证。但在此之前,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先问:这些变化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这种变化为什么重要?
相关统计数据
如果你在网上遇到反跨性别运动者,他们通常会提到“4400%”这个数据的各种变体。我可以引用许多例子,但我将分享的是 J.K. 罗琳在2020年文章中的一个,因为它总结了这些说法中常见的几个特征:
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我自己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之前也不知道——十年前,大多数想要转换性别的人是男性。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反转。英国接受性别转换治疗的“女孩”数量增加了4400%。自闭症女孩的比例在这些数据中显著偏高。
起初,我在 Google Scholar 上搜索这一统计数据,但没有找到相关的研究文章,这表明它并非来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最可能的来源(正如几个人向我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引用了一位英国政客的言论。文章还提到:“在同一时期,男孩的转诊人数从57人增加到713人。”用百分比表达,这相当于跨性别女性/女性化青少年增加了1,250%,但反跨性别运动者似乎从不引用这一数据。
将跨性别男性/男性化青少年的数据用百分比(4400%!)而不是更易理解的方式(增加44倍)来表达,同时没有为跨性别女性/女性化青少年引用类似的数据(1,250%或12.5倍),这表明文章的措辞是故意夸大其词,以引起人们对“女孩”命运的担忧。(我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
两周前,Jonathan Chait在反驳一封表达对《纽约时报》最近关于跨性别问题(包括性别肯定治疗)报道的公开信中,提出了类似于罗琳的担忧,尽管他引用的统计数据来源更为可靠:
“根据WPATH的说法,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青少年接受跨性别护理的频率是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青少年的2.5到7.1倍。”这发生在精神健康危机中,而这场危机对女孩和LGBTQ+青少年的影响尤为严重。
这段引述来自最近的路透社文章,但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和语言似乎出自WPATH最近发布的《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人群健康护理标准》第8版(SOC8),你可以通过该链接下载全文。它出现在第S43页,似乎被挑选出来以产生戏剧性的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我提供了完整的段落:
直到最近,关于青少年性别多样性的流行率信息仍然有限。高中样本的研究显示性别多样性的比例远高于先前的估计,报告显示多达1.2%的参与者认同为跨性别者(Clark等,2014),以及多达2.7%或更多(例如,7%至9%)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报告的性别多样性(Eisenberg等,2017;Kidd等,2021;Wang等,2020)。这些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性别多样性不应再被视为罕见。此外,性别诊所中也报告了按出生性别分配的不均衡比例,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青少年(AFAB)接受治疗的频率比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青少年(AMAB)高出2.5至7.1倍(Aitken等,2015;Arnoldussen等,2019;Bauer等,2021;de Graaf、Carmichael等,2018;Kaltiala等,2015;Kaltiala、Bergman等,2020)。
这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图景,表明跨性别青少年并不那么罕见,而那些“开始治疗”的仅仅是跨性别青少年群体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点得到了SOC8“人口估计”部分(第S23至S26页)中审查的众多研究的支持。在第S23页,WPATH明确指出:
在基于诊所的研究中,关于TGD(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人群的数据通常仅限于接受跨性别相关诊断或咨询的个人,或那些请求或接受性别肯定治疗的人,而基于调查的研究通常依赖于更广泛、包容性更强的定义,基于自我报告的性别身份。
因此,当研究人员引用“开始治疗”或“诊所转诊”的跨性别青少年人数增加或变化时,这些统计数据并不描述跨性别人群总数的变化,而是描述当前正在接受治疗的跨性别青少年这一小部分的变化。为支持这一解释(并与“4400%”之类的危言耸听说法相矛盾),SOC8部分中审查的基于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出接近1:1的比例,唯一的例外是(Lowry等,2018年对性别不符的高中生的调查)显示AMAB青少年的数量是AFAB青少年的三倍。
最近,Turban等人(2022)研究了近20万名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数据,发现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的比例略高(例如,2019年AMAB与AFAB的比例为1.2比1)。
诚然,不同调查之间的比较存在一定困难,因为它们在人口统计数据、所提问题等方面必然有所不同。当然,也可以对某项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出质疑(事实上,一些反对者会采取这种策略!)。但总体趋势似乎很清楚:虽然在跨性别青少年的“诊所转诊”和“开始治疗”中可能存在出生时指定性别比例的变化,但没有实质性证据表明跨性别男性/男性化人数相对于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人数出现了近期的“爆炸式”增长。这并非仅仅是我的观点——以下是WPATH对所有这些人口估计的解释(摘自第S26页):
年轻年龄组中TGD(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个体的比例较大,AMAB与AFAB比例的年龄相关差异可能反映了“群体效应”,这一效应体现了社会政治进步、转诊模式的变化、获得医疗保健和医学信息的机会增加、文化污名减轻以及其他代际间差异性影响的变化。
换句话说,这些数据支持我所称的“污名减少”假设,而不是“社会传染”假设。WPATH在该段中引用的一篇论文(Ashley,2019)进一步补充道:
考虑到GIC(性别认同诊所)人群与性别多样化人群之间的规模差异,社会文化因素对转诊模式的影响是最有希望的解释。未来的研究人员应避免假设指定性别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性别多样化人群中的比例变化。目前没有证据支持AFAB与AMAB青少年比例在整体跨性别青少年群体中发生了变化的观点。
为什么特别强调“女孩”和心理健康?
让我们暂时假设“跨性别社会传染”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如果它确实存在,为什么它应该主要影响跨性别男性/男性化青少年?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包括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对跨性别持怀疑态度的家长和Lisa Littman(她将其重新命名为“ROGD”)——声称它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明确提到了Tumblr、Reddit和YouTube)以及朋友圈。我很确定,跨性别女性/女性化青少年也能接触到这些平台!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受同样的影响呢?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跨性别社会传染”对自闭症和/或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影响尤为显著(正如上文罗琳和Chait的引用中所示,以及Littman原始的未经修正的ROGD论文中提到的)。当然,一些跨性别者(无论是AMAB还是AFAB)确实会经历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被视为性别肯定护理的禁忌症。以下是WPATH SOC8关于心理健康章节中的一段摘录(第S171–S172页;为便于阅读,我删除了所有引用):
一些研究表明,TGD(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人群中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的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医疗上必要的性别肯定治疗的人群中。然而,跨性别身份并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些较高的发病率与复杂的创伤、社会污名、暴力和歧视有关。此外,精神病症状会随着适当的性别肯定医疗和手术护理的实施,以及减少歧视和少数群体压力的干预措施而减轻……解决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的问题很重要,但不应成为获得转变相关护理的障碍。相反,解决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干预措施可以促进转变相关护理的成功,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同样,一些跨性别者也会经历自闭症/神经多样性,熟悉跨性别健康的专业人士会在这两方面同时提供支持(参见例如Strang等,2020年)。WPATH SOC8明确指出(第S37页):没有证据表明由于TGD人群存在心理健康或神经发育障碍而拒绝提供性别肯定的医疗或手术治疗对他们有益。
正如许多在我之前的人指出的那样,“跨性别社会传染”理论的支持者对“女孩”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反复强调,似乎是为了迎合性别歧视和能力歧视的偏见,暗示这些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理解自己,并做出关于自己身体和生活的决定。
但我认为,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我在配套文章中提到的,支配性/多数群体(在此指顺性别者)往往将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视为“被污染的”,并可能“腐化”那些所谓“纯洁”的群体成员。这种无意识的“污染”心态驱动了对被边缘化群体可能具有传染性(例如“变成同性恋”、“跨性别社会传染”)以及性腐败(例如“性欺骗者”、“洗手间捕食者”、“操控者”)的恐惧。[我在这篇文章以及我书中的第7和第8章《Sexed Up》中对这种心态有更深入的讨论。]
通过创造出“被污染的、腐化的、危险的外群体”与“纯洁的、无辜的、脆弱的内群体”之间的巨大差距,想象中的威胁会显得更为恐怖。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恐慌(包括这场最新的反跨性别恐慌)几乎总是围绕着“保护女性和儿童”展开,尤其是那些白人、中产阶级及其他未被标记的群体成员(即“未被污染”,因此是“纯洁的”)。
反跨性别运动者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种心态,将跨性别活动家描绘成“成年男性”,他们所谓地“捕食”(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性别上的)那些无辜而脆弱的“年轻女孩”。将这些“女孩”描绘成因所谓的女性脆弱性、神经多样性或心理健康问题而在精神上不胜任,只会进一步放大她们被想象中的纯真和脆弱性。
或许这一心态最好的例证可以在Abigail Shrier的书《不可逆的伤害:跨性别热潮如何引诱我们的女儿》中找到。该书几乎专注于描述“社会传染”如何肆虐“我们的女孩”,并通过对Ray Blanchard和J. Michael Bailey的采访简要地描绘跨性别成年人为“性变态的男人”。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讨论“操控”,但副标题“引诱我们的女儿”以及“跨性别热潮”这一措辞暗示这些孩子的跨性别身份是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或助长的。哦,我还没提到封面上的漫画:一个小女孩,她的生殖器部位被挖空(暗示她“被玷污”了)。
这种心态也影响了对去转变(detransition)现象的跨性别怀疑论描述。虽然人们因各种原因去转变/重新转变,并走上不同的轨迹,但反跨性别运动者和顺性别媒体制作人似乎最感兴趣的是一个特定的故事:那个“年轻女孩”经历了性别转换,但现在后悔了,通常强调“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肯定护理“毁了”她的生活和身体。媒体对这个叙述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通常淡化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采访对象有些是成年后才转变的,因意识形态原因去转变,和/或与反跨性别团体有密切联系。被忽视的是真正去转变的AMAB个体、那些由于缺乏家庭或社区支持而去转变的人、以及那些对他们过去接受的性别肯定护理不感到后悔的人(因为这些故事不符合“被外部腐化和污染的纯真内群体成员”这一叙述)。
需要明确的是,我不认为每个推动这一叙述或对其产生共鸣的人都故意在进行性别歧视、能力歧视或故意宣扬跨性别恐惧。刻板印象和心态通常在无意识层面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吸引人且难以反驳。但我希望这一部分能帮助读者识别出这种“污染”心态的特征,它如何推动对“社会传染”和“操控”的恐惧,以及它在道德恐慌中的核心作用。
传统性别歧视与获取性别肯定护理的差异
无数研究(其中许多在WPATH SOC8中被审查)一再表明,性别肯定护理对跨性别青少年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对跨性别青少年“开始护理”进行恐吓,不如关心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跨性别青少年能够获得这种护理。与其将其称为“性别比例变化”(这让它听起来像是新的现象),我们应该重新框定为“获取性别肯定护理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一直存在)。
“性别比例变化”或“跨性别社会传染”叙事中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过去的比例(当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占大多数的性别诊所转诊)必须是某种“自然基线”,而我们现在偏离了这一基线。但这些数字一直是偏颇的,正如我在2007年的书《Whipping Girl》中详细讨论的那样。以下是我在那里所做论点的简要概述。
所有跨性别者都会面临跨性别恐惧症。但传统性别歧视(即认为女性化和女性特质低于或不如男性化和男性特质正当)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不同经历的跨性别者。具体来说,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由于性别越轨和转变的方向(向女性化/女性)而往往受到不成比例的关注、审视和妖魔化。在《Whipping Girl》中,我将这一现象称为跨性别女性恐惧症(transmisogyny)。
在《Whipping Girl》一书中,我讨论了跨性别女性恐惧症如何影响媒体描绘,媒体历史上主要集中在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上(因为我们更容易被性别化和戏剧化,以及被描绘成“伪造”),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跨性别男性/男性化个体(导致其隐形)。类似的动态也发生在20世纪的跨性别相关研究和医疗审查中,这些研究和审查主要集中在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上,因为他们被视为更“心理病态”。几十年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女性化的男孩”比“男性化的女孩”更感到不安(Martin,1990;Sandnabba & Ahlberg,1999;Kane,2006;Sullivan等,2018),因此,父母更有可能将前者送去接受心理治疗,而不是后者。(这是在转变治疗而不是性别肯定护理成为常态的时代。)
作为在那个时代成长的人(我是X世代),跨性别的经历深受这些力量的影响。和我这个年龄的许多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一样,我从媒体描绘中了解到了跨性别女性的存在,但由于她们被如此广泛地嘲笑和污名化,我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时期竭尽全力避免成为她们。与我同龄的跨性别男性通常有不同的故事:他们知道跨性别女性的存在,但从未听说过跨性别男性的存在,因此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自己也可以选择转变。这种隐形现象有助于解释当时性别诊所的统计数据,显示跨性别女性的“比例”比跨性别男性高出三倍。
快进到21世纪。随着跨性别污名逐渐减少,跨性别的可见性和意识相应增加,越来越多的跨性别者(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并找到相关信息和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认同为跨性别者的人数(无论是在调查中还是通过接受性别肯定护理)在不断上升的原因。但传统的性别歧视依然非常普遍,正如人们不断努力将跨性别男性/男性化青少年和年轻人描述为“太脆弱、太不理智,无法为自己做出合理决定的女孩”一样。传统性别歧视还推动了跨性别女性恐惧症的刻板印象,认为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极其做作(“是女性的模仿品”)且性动机强烈(“放荡不羁”、“恋物癖者”、“捕食者”、“操纵者”)。许多跨性别女性告诉我,这些刻板印象使她们直到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甚至更晚才敢公开身份——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跨性别女性/女性化青少年在接受性别肯定护理的比例低于跨性别男性/男性化青少年。
为支持这一观点,请考虑这项研究“儿童性别焦虑转诊性别比例的变化证据:来自伦敦性别认同发展服务的数据(2000-2017)”(de Graaf等,2018)。和其他诊所一样,他们观察到了总体上向跨性别男性/男性化个体转诊的变化,但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年龄分叉,3-9岁的儿童中跨性别女性/女性化个体占主导地位,而10-12岁的儿童中跨性别男性/男性化个体占主导地位。在讨论中,他们这样解释前者:
性别转诊年龄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家长对儿子明显的性别变异行为比对女儿更为担忧(例如,担心同伴的排斥)。
对于后者,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目前,青少年中性别比例变化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可能包括对行为男性化的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个体污名较少,相比之下,行为女性化的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个体会受到更多的污名,这使得前者更容易“公开”作为跨性别者身份,并寻求心理健康护理和生物医学治疗。
与“跨性别社会传染”理论不同,我在这里以及配套文章中提出的“污名减少”模型并非一刀切。它是动态的,能够容纳各种形式的污名(传统性别歧视、跨性别恐惧症、能力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等),这些污名可能相互交织,并对每个个体、不同文化或不同时间段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其说是“让人成为跨性别者”,污名的逐渐(或突然)减少可能会影响个体何时以及如何了解跨性别者,他们对这一认知的反应(选择公开身份,或继续隐瞒),以及他们能获得哪些可能性(在年幼时进行社会性别转换,或等待到成年;拥有相对正常的生活,或被迫处于社会边缘)。
我怀疑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是否能改变那些坚决反对跨性别青少年的活动人士的看法,他们无论如何都坚持要否定跨性别青少年的身份。但我希望这篇文章能鼓励其他人放弃过于简单化(并且常常过时的)跨性别叙事,并认识到跨性别者的人口统计、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并不是某种“问题”的“迹象”或“症状”。相反,正如我们的文化一样,我们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本文及其配套文章《所有反驳“跨性别社会传染”的证据》是由我的Patreon支持者们促成的——如果你对此有帮助,欢迎在Patreon上支持我!

目前有0 条留言